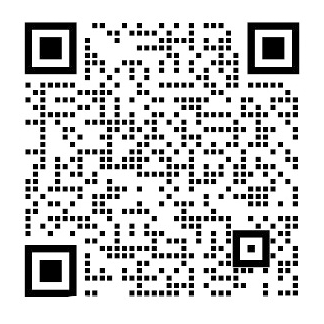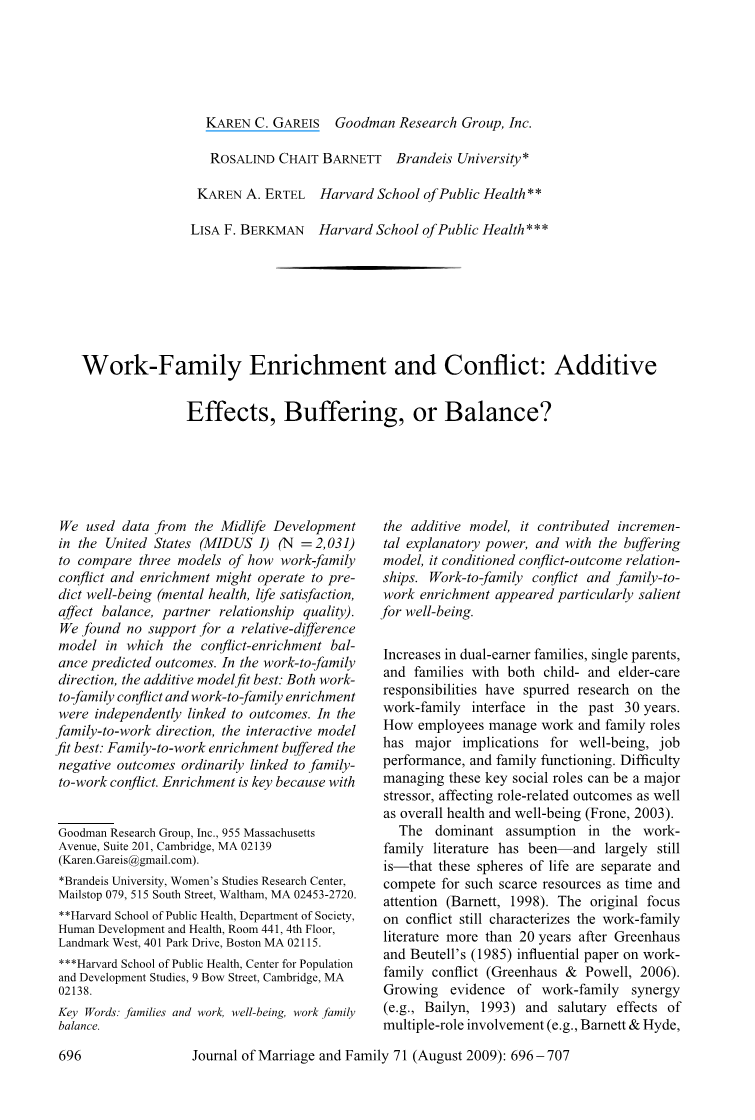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3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工作家庭增益和冲突︰ 附加影响,缓冲或平衡?
我们使用来自美国中年发展 (MIDUS I) (N =2,031)的数据来比较三种模式的关于工作-家庭增益和冲突如何可能运作来预测幸福(心理健康、 生活满意度、影响平衡及伙伴关系质量)。我们发现没有支持的冲突增益平衡可以预测结果的相对偏差模型。在工作-家庭的方向,可加性模型最适合︰ 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增益都独立与结果相关。在家庭-工作的方向,交互式模型最适合︰ 家庭工作增益缓冲了通常与家庭-工作冲突相关的负面结果。增益是关键,因为在附加性模式中,其贡献了增额解释力;在缓冲的模型中,其控制了冲突结果关系。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增益对于幸福显得尤为显著
关键词︰ 家庭和工作、幸福、工作-家庭平衡
在过去 30 年中,双职工家庭、 单亲家庭以及有两个孩子和老年人护理责任的家庭的增加刺激了工作家庭界面研究。雇主如何管理工作和家庭角色对于幸福、工作绩效和家庭功能具有重大的含义。管理这些关键的社会角色的困难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影响了角色相关的结果、整体健康和幸福(Frone, 2003)。
在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文学中,最主导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生活的这些领域是分开的并相互争夺稀缺的资源,如时间和注意力 (Barnett, 1998)。在Greenhaus and Beutell的有影响力的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论文 (1985)后,原始的对于冲突的关注仍普遍存在工作家庭文学超过20年 (Greenhaus amp; Powell, 2006)。关于工作家庭协同作用 (Bailyn, 1993) 和多角色参与的有益影响(Barnett amp; Hyde,2001; Marks amp; MacDermid, 1996)的证据有所增长,然而,这挑战了冲突的假设。工作-家庭学者 (Greenhaus amp; Parasuraman, 1999; Grzywacz amp; Marks, 2000) 呼吁更多地注意工作-家庭冲突的另一面︰ 工作家庭增益或 在一个角色的经验提高在另一角色的生活质量 (Greenhaus amp; Powell, p. 73)。
Greenhaus and Beutell (1985)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双向的,所以一般地,这个术语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每个方向的影响被假定有不同的经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Frone, Russell, amp; Cooper, 1992; Gutek, Searle, amp; Klepa, 1991)。例如,长时间的工作可能预测工作-家庭冲突,而沉重的老年人护理需求可能预测家庭-工作冲突。在同一领域,每种类型的冲突被假定预测角色相关的成果,而两种类型的冲突可能预测一般心理和生理健康 (Frone, 2003)。因此,家庭-工作冲突可能预测差的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冲突可能预测差的家庭关系,而两种形式的冲突可能预测低的幸福感。
相较于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受到较少关注,在概念及经验上仍发展不完全(Frone, 2003; Witt amp; Carlson, 2006),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近期开始弥合这一差距 (例如,Greenhaus amp; Powell, 2006; Grzywacz amp; Bass, 2003)。到目前为止,在术语上仍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Frone, 2003),虽然Carlson, Kacmar, Wayne, and Grzywacz (2006)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类系统。Carlson将术语“Work-Family Enrichment”定义为当发生从一个角色提高另一个角色的绩效和生活质量时,资源和经验被获得。这个定义最好地在数据组中描述了评估我们用于分析的工作家庭界面的积极方面的项目。
工作家庭增益,正如冲突,被定义为是双向的 (Greenhaus amp; Powell, 2006),所以,术语包括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的增益。因此,合作伙伴可能会给您一个建议,以更好地履行工作任务,或在高效工作的一天可能会转化为在家中与家人更周到的互动。对于工作-家庭和家庭-工作增益和冲突的四重分类研究在几项研究中(例如,Grzywacz amp; Marks, 2000)已经得到了实证支持。
虽然很多文学仍将工作-家庭平衡概念仅作为没有冲突 (Frone, 2003),学者最近也开始整合冲突和增益来更充分地描绘的工作-家庭界面的构造。首先,一些理论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是不一定平行的概念;他们可能涉及稍有不同的基本过程和预测稍有不同的结果 (Frone, 2003; Witt amp; Carlson, 2006)。第二,如上所述,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具体化工作-家庭界面的积极方面纳入他们的模型,甚至有的研究人员详述工作-家庭层面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如何可能相互结合并产生结果。例如,Greenhaus and Powell (2006)猜测在有主要影响之外,增益可以缓冲人们从工作-家庭冲突获得的消极后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只是将冲突和增益模拟为独立的预测因子,测试简单的附加关系。然而这种附加模型只是其中几种可能概念化工作家庭界面的方法中的一种。
在其中一个比较不同理论衍出的关于工作-家庭界面的模型的研究中,Grzywacz and Bass (2003)使用了数据模型来自Wave 1 of the National Survey of Midlife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DUS I)的数据审查结合冲突和增益来预测二歧精神错乱的结果的两种方式。这一理论框架是基于家庭的弹性理论 (Patterson, 2002),理论阐明了一个家庭的资源或能力让它在面临的风险中成长。(作为增益运作) 的资源可能允许家庭评估 (作为冲突运行) 的要求是毫无威胁性的,不需要进一步关注。这种称为消除战略因为资源允许某一因素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被定义为无威胁性。操作上,这一过程反映在冲突和增益的独立影响 (或附加) 模型上。Greenhaus and Powell(2006)假设的缓冲关系反映在交互作用 (或缓冲) 模型也是一种消除策略,在这一模型中增益缓冲了消极后果到一个较好的低于高冲突控制的程度。例如,可能有附加的影响,其中当员工因为过多的工作需求而缺少家庭活动时,冲突可能发生在家里,但与此同时,该工作获得奖励将使员工在家中成为更好的伴侣。在交互式或缓冲影响中,当员工缺少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家庭活动时,一个更好的伴侣可能呈现的更强的缓冲作用,
另外,增益可能允许家庭承认冲突作为一种威胁,但作为一种可控的程度评价的基础,家庭功能 (增益) 超过这些要求(冲突)。这种情况称为同化战略,因为威胁是被承认的,但被认为是可控的、是可以被吸收并加入家庭的结构和功能的。例如,雇员可能会明确地评估在何种程度上,工作努力会提供家庭需要,从而可以忽略家庭问题可能会使其在工作上分心。同化战略明确侧重于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因此,它可以作为相对差异 (或平衡) 模型被实施,其中的预测因素是增益减去冲突。
Grzywacz and Bass (2003)发现冲突和增益对于抑郁症和酗酒问题有附加影响,但对焦虑障碍有互动影响。也就是说,增益缓冲了冲突和焦虑的负面关系。因此,不同工作-家庭界面的模型支持不同的结果,但都反映了消除,而不是同化。Grzywacz and Bass表明确切的过程可能不同于结果。具体而言,他们认为,焦虑比沮丧对于面对家庭压力时家庭资源的缺失更敏感。这些结果表明,很大一部分的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阐明,在这样的研究成果下,冲突和增益有附加影响与交互式或缓冲的效果,或是否有为其相对差异或平衡的模型提供了最合适的结果。
我们所知,没有其他的研究者比较了不同工作-家庭界面的模型。我们拓展了Grzywacz and Bass (2003)分析时使用的MIDUS I数据集比较以冲突和增益作为预测因素的社会性情绪幸福的结果(包括自我评价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影响平衡和伴侣的受访者,伙伴关系质量)的添加、互动和相对差分模型。我们审查不同的结果因为Grzywacz and Bass发现基本流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还探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一套相互关联的相对罕见的心理疾病(在 MIDUS I中只有 3.8% - 13.9%有疾病的受访者被Grzywacz and Bass所审查)以外的更多日常社会性情绪幸福的结果。
MIDUS I对于解决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尤为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家的数据集,具有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的措施。进一步,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健康的研究,它包含各种幸福结果的数据。(注意,最近可用的 MIDUS WAVE 2 数据不适合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与Grzywacz and Bass, 2003分析比较; 进一步,自然减员和受访者退休已经减少了一半在WAVE 2的合格样品受访)
为了与Grzywacz and Bass (2003)一致,在我们的分析中,协变量为年龄、 性别、 种族或族裔少数群体地位、 教育、 收入、 合作的地位、 年轻铅中毒,自雇,存在和工作时间。性别是包括的,因为工作和家庭的责任是性别化的(Barnett, 1998)。幸福结果可能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有所差异 (Shmotkin,1990)。工作家庭经验显然受合作伙伴和年幼儿童的存在和工作时间制约(Barnett; Kossek amp; Ozeki, 1998)。最后,根据Frone (2000),年龄、种族或族裔少数群体地位、 教育、 收入和自我就业都包括其中,因为工作家庭经验和幸福都与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社会经济因素和就业情况相关(Grzywacz amp; Bass)。
除了Grzywacz and Bass (2003)的协变量,我们添加负面影响作为神经质、 用于解决共同方法偏差 (Burke, Brief, amp; George, 1993)。自我报告措施的预测因素和结果可能反映共同的基本反应偏见(Allen, Herst, Bruck, amp; Sutton, 2000)。尽管关于是否消极情感最好视为一个方法论滋扰变量 (Burke etal)或倾向性的变量(Grzywacz amp; Marks, 2000)的问题仍有疑问,但显然这对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中的负面情绪控制极为重要。
方法
参与者
MIDUS WAVE 1在毗连美国的地区收集了1995 年- 1996 年,年龄在 25 岁 – 74岁的讲英语成年人的数据。核心样本通过随机数字拨号。我们的分析包括了采用完成工作家庭措施的核心样品受访者(N = 2,031; 1,075位男性,956位女性)。样品容量中有87.6%白人,6.6%黑人,1.3%亚洲人; 4.5%作为多种族或其他自我描述。约有三分之一 (34.0%) 有本科学位或更高。中等家庭年收入是47,000美元。23.8%的样本家庭收入 le;25000美元及 37.8%的样本家庭收入 le;35,000 美元。平均而言,受访者每周工作小时为44.2小时 (SD = 14.6)。大多数 (64.3%) 已经结婚或同居; 其中,74.9%每周平均与工作伙伴相处41小时 (SD = 13.4);因此,48.2%的人为双职工夫妇。有未成年的子女在家中的样本为44.2%和 34.7%每个月花时间协助父母;其中有16.8%同时分在这两组中,因此共同承担赡养老人和照顾子女的责任。
程序
如上所述,样品通过随机数字拨号并有一个年龄在 25 岁- 74岁的家庭成员选择作出回应获得。老年人和男性过度取样以获得良好的分布对交叉分类的年龄和性别。如果受访者没有完成面试,则没有其他家庭成员被选中。受访者完成了30分钟的电话采访和两个45页邮寄问卷。电话采访的回应率为70%,其中87%完成问卷的整体回应率为60.9%。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分析中使用的样本权重,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变量之间的联系,在此示例中,因此,我们相对漠不关心的研究变量的人口患病率。
措施
通过平均答复回答了的项目,所以即使受访者跳过一些项目,他们还收到一个分数,取得了多项分数。有极少的数据缺失,然而;虽然对于大多数项目跳过率为0.0%~ 0.9%,但高于2.0%的伴侣受访者跳过关系质量的项目。
工作-家庭和家庭-工作冲突和增益被四项规模开发的 MIDUS I的研究人员评估。项目包括“当你在家时,工作忧虑或问题使你分心”,“在家的责任使你减少了你可以投入工作的努力”“拥有在工作上好的一天可以使你在家时成为更好的伴侣”和“与家中某人沟通帮助你处理工作问题”。问题评分从1 (从来没有) 到 5 (所有时间)。工作-家庭冲突、增益和家庭-工作冲突和增益的信度Cronbachs alpha;s分别为.82,.72,.79 和.68。
受访者将他们心理或情感上的健康评为从 1 (差) 到 5 (优秀); 这种单项措施研究的健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般都与更长的措施密切相关,有可比性的可靠性,以及并发和区分效度 (例如,DeSalvo et al., 2006)。
受访者对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02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