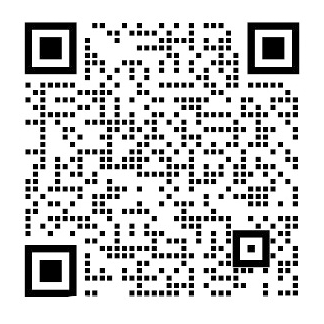文献翻译原文
Extracted from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which is written by Hans Robert Jauss and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Timothy Bahti. Hans Robert Jauss is a German literary theorist, and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esthetics. The excerpt is from the 40th page to the 48th page.
The 40th page to the 48th page:
IV
The beginnings of the Formalists, who as member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 (Opoyaz) came forth with programmatic publications from 1916 on, stood under the aegis of a rigorous foregrounding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 raised literature once again to an independent object of study when it detached the literary work from al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like the new structural linguistics defined its specific result purely functionally, as “the sum-total of all the stylistic devices employed in it.9 The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poetry” (Dichtung) and literature thus becomes dispensable. The artist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is to be ascertained solely from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oetic and practical language. Language in its practical function now represents as “a nonliterary series” all remaining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ing of the literary work; this work is described and defined as a work of art precisely in its specific differentiation (ecart poetique), and thus not in it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to the nonliterary ser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etic and practical language led to the concept of “artistic perception,” which completely severed the link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ved praxis. Art now becomes the means of disrupting the automatization of everyday perception through 'estrangement' or 'defamiharization' (ostraneniye). It follows that the reception of art also can no longer exist in the naive enjoyment of the beautiful, but rather demand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orm,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operation. Thus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in art appears as an end in
itself, the “tangibility of form” as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operation” as the principle of a theory. This theory made art criticism into a rational method in conscious renunci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thereby brought forth critical achievements of lasting value.
Another achievement of the Formalist school meanwhile cannot be overlooked. The historicity of literature that was at first negated return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Formalist method, and placed it before a problem that forced it to rethink the principles of diachrony. The literariness of literature is conditioned not only syn chronically b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oetic and practical language, but also diachronically by the opposition to the givens of the genre and the preceding form of the literary series. When the work of art is “perceiv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other works of art an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m,” as Viktor Shklovsky formulates i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 of art must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ts relation to other forms that existed before it did. With this the Formalist school began to seek its own way back into history. Its new project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the old literary history in that it gave up the formers fundamental image of a gradual and continuous process and opposed a dynamic principle of literary evolution to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tradition. The notion of an organic continuity lost its former precedence in art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tyle.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evolution discover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dialectical self-production of new forms,” describing the supposedly peaceful and gradual course of tradition (Uberlieferung) as a procession with fracturing changes, the revolts of new schools, and the conflicts of competing genres. The “objective spirit”of unified periods was thrown out as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According to Viktor Shklovsky and Jurij Tynjanov, there exists in each period a number of literary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where in one of them represents the canonized height of literature”; the canonization of a literary form leads to its automatization, and demands the formation of new forms in the lower stratum that 'conquer the place of the older ones,' grow to be a mass phenomenon, and finally are themselves in turn pushed to the periphery.
With this project, that paradoxically turned 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evolution against the organic-teleological sense of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evolution, the Formalist school already came very close to a new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the origin, canonization, and decay of genres. It taught one to see the work of art in its history in a new way, that is, in the changes of the systems of literary genres and forms. It thus cut a path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that linguistics had also appropriated for itself: the understanding that pure synchrony is illusory, since, in the formulation of Roman Jakobson and Jurij Tynjanov each system necessarily comes forth as evolu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evolution inevitably carries with it the character of a system.' To see the work in its history, that is, comprehended within literary history defined as “the succession of systems,” is however not yet the same as to see the work of art in history, that is, in the historical horizon of its origina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The historicity of literature does not end with the succession of aesthetic-formal systems;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like that of language, is to be determined not only immanently through its own unique relationship of diachrony and synchrony, but also through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general process of history.From this perspective on the reciprocal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译文
节选自汉斯·罗伯特·姚斯的《走向接受美学》,该书由蒂莫西·巴赫蒂翻译自德语。汉斯· 罗伯特·姚斯是德国文艺理论家,也是接受美学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之一。节选了第40页到第48页的内容。
第40页到第48页:
四
形式主义者作为“诗歌语言研究会”的成员,从1916年开始发表团体纲领起,形式主义者开始发展,严格地保护着文学艺术特征的前景。形式主义的方法理论的将文学从一切历史条件中分离出来,像新的结构语言学一样,在功能上解释文学的特殊效果,将文学的定义为“所有风格技巧的总和”。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诗”与文学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可有可无。文学的艺术性只能由诗性语言和实践性语言的对立来确定。语言的实际功能现在表现为“一种非文学系列”,保留了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一部作品被描述和定义为的艺术作品(诗歌),是因为它的独特差异性,而与非文学系列的关系。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的区别导致了“艺术感知”的概念,它完全切断了文学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艺术现在通过“疏离”或“陌生化”成为打破日常感知自动化的手段。由此可见,接受艺术也不再能够存在于对美的朴素的欣赏之中,而是要求形式的差异性和对操作差异性的认识,因此,艺术中的感知过程似乎在于其本身,以“形式的可感知性”作为其特有的特征,“以发现差异性的操作”作为一种理论原则。这一理论使艺术批评成为自觉放弃历史知识的理性方法,从而产生了具有持久价值的批判性成果。
与此同时, 形式主义学派的另一项成就不容忽视。起初被否定的文学的历史性,也随着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扩展而回归, 这个问题,迫使形式主义学派重新思考历原则。文学的文学性不仅是由诗歌语言与实践语言的对立同步制约的共时性, 而且也是由对体裁的对立和文学系列的前体形式的对立的历时性。正如维克托· 舍克洛夫斯基所规定的那样, “当一个艺术作品,在其他艺术作品的背景下被感知并与之结合时” 对艺术作品的解释也必须考虑到它与之前存在的形式。因此,形式主义的学派开始回到历史寻求自己的道路。它的新项目不同于旧的文学史, 因为它放弃了前者的渐进和持续过程的基本形象, 反对文学演变的动态原则, 以经典的传统概念。有机连续性的概念在艺术史和风格史上失去了以前的优先地位。分析文学演变,发现了文学史上 “新形式辩证的自我产生,”的辩证自我生产, 将所谓的传统和平而渐进的过程描述为一个分裂的过程, 即新学派的反抗, 和各流派的竞争。统一时期的 “客观精神” 被认为是形而上学而被摒弃。根据维克托· 舍克洛夫斯基 和 尤· 蒂芙尼诺夫的看法, 每个时期同时存在一些文学流派, '其中一种流派代表了文学的最高高度';这一文学形式的高度导致它本身的僵化, 要求在下层形成 '征服老文学形式' 的新形式 ',这就是变成了一个大众现象, 最后是自己被推到了边缘。
这个方案矛盾地把文学进化论的原则与古典进化论概念的有机目的论意义上对立起来, 形式主义学派已经有了非常接近于在起源,标准,流派衰变的领域中对文学的新的历史理解。它告诉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其历史上的艺术作品, 即文学体裁和形式体系变化的角度去看。因此, 形式主义开创了一条通往一种理解的道路, 对语言学也一样有用: 这种理解, 即纯粹的共时是幻想的, 因为在 罗曼bull;雅各布逊和Jbull;泰尼亚诺夫的表述中, “每一个系统都必然以进化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演变不可避免地带有系统的特征”。从历史看文学作品, 是理解文学历史中定义的 “系统” 的继承, 与看到历史上的艺术作品还不一样, 也就是说, 在它的起源的历史视野中, 就是从作品起源、社会功能、历史影响区理解艺术作品。文学的演变和语言的演变一样, 不仅要取决于自身独特的历时性和同步性, 也要取决于它与整个历史进程的关系。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各有长处, 可以看出来两个理论有不足之处。需要互为补充,不能单看其中一个。一方面可以理解在制度的历史变迁中文学的演变, 另一方面可以理解实用历史在社会条件的过程性的联系, 那么难道也不可能把 “文学系列”和“非文学系列”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相互关系, 来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而不强迫文学消耗在其作为艺术的特点, 使其只一种模仿和评论的功能吗?
五
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看到了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即再次讨论文学史问题,而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方法的争论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试图弥合文学与历史之间、历史与美学之间的鸿沟,从这两个学派停止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方法是在生产美学和表现美学的封闭循环中构思文学事实。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失去了一个方面,这与美学特征,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不能分开的,这个方面就是文学接受和影响。读者、听众和观众——总之,无论在那种文学理论中,接受因素的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待读者——如果有的话——与对待作者没有什么不同:它询问他的社会地位,或者试图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结构中认识他。形式主义学派只需要读者作为一个感知主体,遵循文本中方向,以区分(文学)形式或发现(文学)过程。它假定读者像语言学家有理论上的理解,能思考和掌握艺术手法;相反,马克思主义学派坦率地将读者的自发经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兴趣等同起来,尝试发现文学作品中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的关系。
然而,正如瓦尔特·布尔斯特所言:“文本从来不是写出来为语言学家阅读和说明语言学用的,”或者我补充一点也不是为历史学家阅读和解释历史而写的。这两种方法都缺乏真正的读者,这些读者对于美学和历史的知识都是无法改变的:而文学作品注定是要为这些的主要受众而创作的。
即使是评论一部新作品的评论家来说,根据一部早期作品的积极或消极标准构思作品的作者,以及根据其传统对一部作品进行分类并加以解释的文学史家,在他们与文学的反射关系重新变得有生产力之前,他们是最先的读者。在作者、作品和公众的三角关系中,大众不是被动的那部分,不仅仅是反应链,而是自身成为历史能量的构成。如果没有受众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其调解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不断变化的经验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永远有着从简单的接受到转变为批判性的理解,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接受,从公认的审美标准转变为超越它们的新的生产。文学的历史性和它的交际性特征先设定了对话,然后设定了作品、读者和新作品之间的过程性关系,可以在信息和接收者,以及问题与答案、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中构思新的作品。因此,如果把文学作品的历史序列理解为文学史的连贯性问题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法,就必须打开在过去文学研究方法封闭的生产圈和表现圈,向接受和影响的美学开放。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被动接受与主动理解、经验形成之间和新的产生调节,如果以这种方式在形成一种连续性作品和观众对话的视域中与观察,那么文学的美学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会不断得到调和。因此,历史主义从过去到现在的文学经验之间的线索被绑在一起。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既有美学意义,又有历史意义。其美学意蕴在于,读者对作品的第一次接受,包括了对其审美价值与已读作品的比较的检验。其明显的历史含义是,第一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接一代的接受中得以保持和丰富;这样,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会得到确定,其审美价值就会显现出来。在这一接受历史的过程中,对过去作品重新欣赏是与过去和现在的艺术之间、传统的评价和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不断协调、同时发生的,文学史学家不能逃避这个过程,除非他不关心指导他理解和判断的前提。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的文学史的价值将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审美经验积极参与过去的不断起到作用。这要求接受美学一方面反对实证主义文学史的客观主义,有意识地形成一种研究理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古典主义研究相对,如果不打破已经被接受的文学经典的标准的话,就必须进行批判性的修改。接受美学有明确的规定已经开始建成一种规范的标准和文学史的必要复述,从个体作品接受的历史到文学史的这一步,必须引导我们将作品 的历史延续当作并且描述为作品在确认和证明文学的内力,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史前的现时经验,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从这一前提出发,如今关于文学史如何以方法为依据并重新编写的问题,我将是在以下七篇论题中论述。
六
论题一:文学史的更新需要我们去除对历史客观主义的偏见和传统生产和再现美学的基础,确立一种接受与影响的美学。文学的历史性不是事后建立在“文学事实”组织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有经验之上的。Rbull;Gbull;柯林伍德在批判历史上盛行的客观性思想时提出的假设——“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头脑中对过去思想的重新制定”——他的假设甚至对文学史更有说服力。因为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是“客观”描述孤立历史中一系列事件,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和特殊性。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对象,它在每个时期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同样的观点。它不是一个纪念碑,不单单揭示其不受时代影响的本质。它更像是一首管弦乐,在读者中引起了新的共鸣,它将文本从文字的材料中解放出来,带入当下时代中:“词语,在交谈的同时,必须创造一个能够理解它们的对话者。文学作品的这种对话性也确定了语言学理解只能在与文本的永久对立中存在,而不能被简化为对事实的了解。语言学的理解始终与解释有关,而解释必须以理解对象、反思和描述完成新的理解时刻作为其目标。
文学史是一个审美接受和生产的过程, 生产是文学文本在接受读者、反思性评论家和作者在其持续的生产力方面实现的。在传统文学史上, 不断增长的文学 “事实”, 只是这一过程所遗留下的;它只是收集和分类的过去, 因此根本不是历史, 而是伪历史。任何把一系列这样的文学事实当作文学史的一部分的人, 都是将艺术作品的多事之秋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克莱辛·德·特洛依斯的《波西瓦尔》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并不像大约同时发生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样具有历史性。这不是一个“事实”,可以用一系列的情景先决条件和动机所造成来解释, 可以重建的历史行动的意图以及这一行动的必要和次要后果。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除了观察者之外存在的一系列派别的、独立的事件。《波西瓦尔》成为文学事件,只是因为它的读者, 带着对他的早期的作品的记忆来读克莱辛的这部最后的作品, 并且将它和其他之前的作品和知道的其他作者作品相比较, 因此认识到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也获得了评价未来作品的新标准。与政治事件不同的是, 文学事件没存在于自身而使后代逃脱不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文学事件只有在那些随后来的或再次对其做出反应的人——如果有读者想要再次欣赏或者有些作者想要模仿,超越或者反驳这个作品——才能继续产生影响效果。文学作为一种事件的一致性,主要是在当代和后来的读者、评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上进行调节。能否以其独特的历史性来理解和再现文学史,取决于这种期待视野能否被具体化。
七
论题2:从对体裁的预认识, 从已经熟悉的作品的形式和主题, 从诗歌与实践语言之间的对立产生了期待系统,如果描述了一部作品在其历史时刻出现的客观预期体系中的接受和影响,对读者文学经验的分析,就可以避免心理学的威胁陷阱。
我的论题反对一种普遍的怀疑观——怀疑对审美影响的分析是否能接近艺术作品的意义, 或者最好能超过简单的趣味社会学。雷内·威勒克尤其对 I、A-理查德的文学理论提出了这样的怀疑。威勒克认为, 无论是一时的、唯一的个人的意识状态, 还是像J·穆卡洛夫斯基所假定的那样一部艺术作品的效果那样, 是一种集体的意识状态,都不能通过经验主义手段来确定。罗曼·雅各布逊以想用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来取代“集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一种规范体系的形式存在于每一部文学作品中,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以接受者的言语的形式实现——尽管这种体系并不完整,也从未作为一个整体。确实, 限制了影响的主观性, 但它仍然留下了一个问题, 即读者使用哪些资料可以用来理解某一特定作品对特定公众的影响, 并将其纳入规范体系。同时, 有一些以前从未想到的经验主义手段是——文学资料, 使人们能够确定每一部作品的观众的具体态度 (这种态度在心理反应和个人主观读者的理解之前)。就像每一次实际经验一样, 对于一部先前不为人知的作品,第一次文学体验也需要 “一种先见之明,这种先见之明是经验本身的一个要素,在此基础上,我们所遇到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可体验的,因为它是可读背景下的经验。”
一部文学作品,即使以新的姿态呈现,在信息真空中也绝对不是的新东西,而是通过预告、明示或暗示性的信号、熟悉的特征或隐含的典故,为读者提供易于接受一种非常具体的接受方式。它唤醒了读者对已经读过的东西的记忆,使读者产生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开始唤起了读者对“中间和结尾”的期待。在阅读的过程中,这种期待根据体裁或文本类型的特定规则,可以保持不变,或者被改变,重新定向,甚至具有讽刺意味地实现。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个文本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只有一个任意的一系列主观印象,而是特定指令执行过程的直接感知,可根据其构成的动机和理解触发信号得以理解,而且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文本语言学。如果与Wbull;Dbull;斯丹普尔的观点相同,将一个文本最初的期待视野定义为示范同位素,转置到一个内在结构的期待视野,话语增长扩充了这种表达,那么接受的过程就能用扩张了的符号系统来描述,实现系统本身的发展和修正。视野的不断建立和变化的相应过程也决定了个体文本与流派后续文本的关系。
新的文本为读者 (听众) 唤起了期野视野和对早期文本所熟悉的规则, 这些期望和规则在变化、更正、修改, 甚至只是再生产。变化和修正决定了范围, 而改变和再生产决定了类型结构的边界。对文本的解释接受总是以审美感知经验的背景为前提:只有首先澄清了条件下文本理解的视野影响的跨主观转移, 才能有意义地提出解释的主观性和不同趣味或读者层次的主观性的问题。
这种文学历史参照系的客观能力的理想案例是, 这些作品唤起了读者的期望视野, 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由一种传统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815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中国古诗词的意象表达与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词译著为例开题报告
- 论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豪杰译现象——以《黑奴吁天录》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文献综述
-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开题报告
- “言语”和“静默”外文翻译资料
-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电影翻译的力量外文翻译资料
- 从个人成长视角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角阿米尔的人物性格外文翻译资料
- 个人旅游博客作为研究跨文化交往的文本:来自津巴布韦的美国sojourner博客的试点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接受理论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的比较研究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On DifferenceTranslation Of E-C Plant Metaphors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