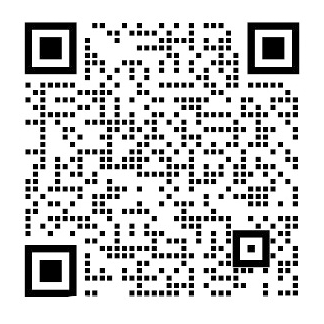市场社会主义的劳动政治
——广州国有工人的集体无为和阶级经验
原文作者:Ching Kwan Lee 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在中国,劳工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主人”正饱受失业之苦。官方登记的城镇国有工人失业人数为525万人,另有2000万人已成为过剩或“下岗”(下岗)工人(1996年11月9日,《中国劳动报》)。劳动部门从1995年年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再就业来应对这些劳动力,主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如食品服务、交通运输、制造业、零售业和旅游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广东劳动报,1995年12月3日)。官方认识到大量的失业者和被裁员,被称为中国媒体的“两类工作人员”,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国家工人的困境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贫困工人”中,即新的城市贫困人口,他们的工资或养老金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一项针对13个省份的调查发现,超过10%的工人在五个省份处于“困境”,在另外6个省5%到10%的工人处于“困境”。无论城镇居民的就业状况如何,未支付的工资和养老金都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中国分析第1577号,1997年1月15日:4-5)。
在改革前的时代,国家工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贵族(Walder,1986)。然而,由于十多年的城市市场改革,他们被毫不客气的赶下来。工资改革,劳动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使得国有工人不再享有终身的雇佣权利,而是按照以市场导向的合同来工作(李培林,141;《北京周报》,1995年4月3日至16日(12月14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新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存在低效率和低竞争力的问题,其工资水平平均落后于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合资企业。国有工人已成为改革中工人阶级中最为艰苦的部分:他们的强烈不满有时会在抗议和罢工中得到表达,迫使政府放慢对企业破产的推动,为失业者设定最低生活津贴水平(远东经济评论,1995年8月31日:40)。
工人们在1989年民主运动(Walder and Gong, 1993)的大规模集会之后,工人们的斗争似乎有增无减。根据官方工会统计数据,1990年大约有1620起仲裁劳动争议(包括减速)事件,涉及37450名工人。从1990年到1991年,集体(10人以上)静坐、减速、罢工、抗议,提出申诉的事件增加了87%,这一比率在1992年至1993年间有所上升(李培林1995:170-71)。仅在1993年,仲裁劳动纠纷就达12358起,其中公营企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远东经济评论,1994年6月16日:32)。
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工业就业和抗议活动都有明显的地方差异。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湖北、湖南、辽宁,以及在地理分布、纺织和煤炭开采方面的工业(程明,1994年4月:30-31;刘1996:128)。一位作家评论道:“经历过动乱的省份大多是中国中部的内陆省份,包括四川hellip;hellip;标题列表....在动乱中占据前13位的省份中,有11个hellip;重工业公司比轻工业公司多hellip;这些公司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生产商品工业、陈旧的设备、过度消耗能源、自给自足、就业不足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第124页)。在沿海和南方城市,劳工斗争集中在外资企业,主要涉及农民工。例如,上海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5年,涉及外国公司的仲裁劳动纠纷增加了三倍,1996年上半年,在200起劳动纠纷中,80%涉及外国投资者(民报,1996年10月18日)。在广东,为抗议外国资本家的虐待而在外资工厂举行的自发罢工和罢工已在新闻界得到广泛报道(见《现代企业日报》,1996年8月18日;羊城晚报,1995年3月22日;《民报》,1996年12月4日及9月18日)。1993-94年间,深圳发生了1100起劳资纠纷,其中90%发生在外资企业(Liu, 1996: 127)。
工人政治的日常形式
除了偶尔的罢工和抗议,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各种形式的劳工政治所标志。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阐明这些日常政治中不那么明显和难以量化的因素。我分析改革时期国家工作人员政治的两个关键概念是“集体不作为”和“阶级经验”。这些概念可能更清楚地反映工人政治模式的本质比聚合数据的公共示威,投诉信件,罢工和静坐,因为他们更系统引起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性质,因此更多的分析意义在理解劳动与政权的变化关系。社会学家周学光(1993)认为,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和集体反抗的特殊形式。国家对社会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对遵守规定提供的有系统的积极激励严重限制了基于西方有组织利益的集体行动。周提醒我们注意“集体不作为”的政治意义:冷漠、不服从、逃避公共责任、缺乏热情、旷工和工作效率低下。这些都是以个人为基础,采取逃避国家控制而不是公开对抗的形式。这些行动是政治行动,因为它们受到国家的认识和反应,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并影响国家开采资源的能力。我将运用这一洞见来说明,当今中国劳工政治的一种关键形式是,在追求工人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无组织但集体的不作为汇聚在一起。
第二种形式的劳工政治与其说与行为有关,不如说是与文化有关。有一种关于劳动经验的政治,涉及一种对现实的霸权建构与普遍持有的“情感结构”和另类理解之间的竞争。经验是继e.p.汤普森(1966)开创性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劳工学者的关键词。一般来说,这个词指的是“广阔、多元、矛盾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在经历事件的过程中权衡并赋予其意义。传统、文化和语言决定了工人对经济和政治变化的集体反应和理解(Sewell, 1980, 1990)。社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概念将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允许阶级以外和阶级之前的身份形成(如古尔德,1995)。中国劳工问题迫使我们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去看:社会主义的经验如何调解中国工人的反应,它的撤退和随之而来的市场优势?过去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抵制或重新解释官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文化武器,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对其当前转型的批判?
文化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雷蒙德·威廉姆斯(1977)所说的“情感结构”。尽管“情感结构”听起来难以捉摸,而且是学术性的,但它在中国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官方和大众话语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媒体上出现了许多报道,表达了官方对工人“极端不稳定”情绪、心理“失衡”、“非理性”情绪以及这些情绪所代表的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指向了新兴的集体冲动,这些集体冲动尚未被清晰地表述为一种形式良好的反霸权,而是“意识和关系的情感元素:不是对思想的感觉,而是作为感觉的思想和作为思想的感觉:一种现实的意识”(威廉姆斯,1977:132)。“感觉的结构”不是反对认知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而是关注它们相互交织的本质,尤其是当它们处于“被体验为私人的过渡到被承认为社会的过渡”(Rosaldo, 1989: 107)。我的许多采访都充满了工人们的愤怒、愤慨和绝望的表达,这些表达交织在他们的推理和论点中,所有这些都必须作为他们集体经验的一部分加以分析。
广州工人的实际情况
我的实地研究是在广东省省会广州进行的。1994年,广州人口620万,其中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约78.1万人。登记失业人数为12.3万人,另有15万名工人- -占国营企业雇员的10%至15%——是国营企业的下岗雇员(广东劳动报,1995年11月12日)。作为一个在改革、特别是私营部门发展方面走在别人前面的省份的省会,广州在统计上可能不具代表性,但在理论上具有说明性。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相比,上海在推动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方面走得更远,这使得它成为检验市场发展对工人政治影响的一个有益案例。从这样一个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能不是因为它们的典型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因果逻辑(Glaser and Strauss, 1967: 63)。与内陆省份相比,应突出广州(或广东)的两个特征。
首先,由于广东在民营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工人在全省参与市场经济“第二经济”的机会相对多于其他地区的工人。1992年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广东有2万多家私营企业,雇用了大约30万名工人。这些数字分别占全国总数的22%和17%。这些私营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占比(1992年5月22日《文汇报》)。在JPRS-CAR-92-038, 1992年5月)。1992年,广州市共有私营企业3877家(不包括数量较多的个体企业),从业人员4.2万余人。个人与私人部门的增长不仅有利于吸收大量失业,失业,和赚钱的求职者(Ikels, 1996: chap.5),但也提供了选择,平行,或交替就业状态的工人。上世纪80年代末,劳动局在多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广州的第二职业就业率高于重庆、天津和上海。
其次,广东对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早期开放,吸引了大量工人从北方省份南迁,使广东的劳动力比内陆省份更为分散和多样化。早在1984年,广州就成为14个给予香港、澳门等地国际及海外华人投资者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之一。其结果是,到1991年,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占广东工业产品和服务总值的23%。在1996年广东省1100万外来务工人员中(《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4月4日:19日),大多数人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找到了工作,28万人进入了广州的城市国家和集体企业。事实上,在广州,纺织行业的工人有一半,橡胶行业的工人有三分之一是“外来工”(外来工)。总之,市场机遇和阶级分化可能使广州的国家劳动关系具有其特殊性。
外文文献出处:《现代中国》,第24卷第1期(1998年1月),第3-33页
附外文文献原文: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Ching Kwan Le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bor by unemployment among the ranks of state workers, the proclaimed masters of the Chinese state. Five and a quarter million urban state workers are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unemployed, and another estimated twenty million have become surplus or 'off-duty' (xiagang) workers (Zhongguo laodongbao, 9 Nov. 1996). Labor officials have responded by launching a nationwide reemployment campaign since mid-1995 to absorb these laborers, mainly by developing labor-intensive, tertiary sectors such as food services, transport, domestic services, retailing, and tourism (Guangdong laodongbao, 3 Dec. 1995).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the massive number of the unemployed and the redundants, who are referred to as the 'two categories of staff in the Chinese press, reveal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The plight of the state workers is also to be found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mpoverished workers,' the new urban poor whose wages or pensions are falling far behind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A survey of thirteen provinces has found that more than 10% of workers are 'in dire straits' in five provinces and 5% to 10% in another six. Unpaid salaries and pension entitlements have affect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urban resi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China Analysis no. 1577, 15 Jan. 1997: 4-5).
In the prereform era, state workers were the labor aristocrats Chinese socialism (Walder, 1986). However, as a result of more a decade of urban market reforms, they have been unceremoniously dethroned. The introduction of wage reforms, the labor contract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ve that state worke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3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571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