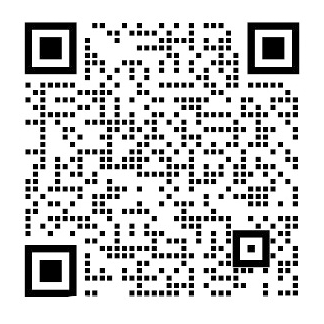Article
Are they guilty of their parental behavior? Parenting forms constructed in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court cases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16, Vol. 15(4) 518–532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473325015595459 qsw.sagepub.com
Vered Ben-David
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t. Louis, MO, USA
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s forms of parenting constructed in Israeli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TPR) cases, and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ir construction, based on a 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 of 130 TPR cases. The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due to lack of clearly-defined evaluation criteria, judges and professionals engage in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processes related to the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rough constructions of non-normative parenting, biological parents are depicted, in court, not only as dysfunctional and parentally unfit but also as lsquo;lsquo;guilty.rsquo;rsquo; Four cate-gories of such parenting were identified: impaired, lsquo;lsquo;failed,rsquo;rsquo; dangerous and harmful. The perception of guilt resulted from the courtsrsquo; attribution of parental behavior to pathologic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ile ignoring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poverty and stress. The study discusses how negative views of parenting impact on legal decisions aimed at serving the childrsquo;s best interests and consequen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and legal practices.
Keywords
Parental capacity,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qualitative research, adoption, court decis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Vered Ben-David, 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Campus Box 1196,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O 63130, USA.
Email: vered_bd@hotmail.com
|
Ben-David |
519 |
Introduction
In most jurisdictions,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TPR) proceedings are initiated against the biological parents by the state when there is evid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CM) and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arentsrsquo; parental incapacity will not change, in a reasonable time frame and despite the social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 family (Benjet and Azar, 2003; Wattenberg et al., 2001). TPR represents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hild protection response to CM. The various professionals who take part in the legal proceedings, such as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psychiatrists,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provide the courts with assessments of the child and the parents (Budd, 2001, 2005; Budd et al., 2006). The courts then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e parents are capable of providing adequate care and custody for their child, whether the parental behav-ior and/or condition are likely to change in a reasonable time period and the childrsquo;s best interests (Azar et al., 1995, 1998; Barnum, 1997; Budd et al., 2013; Grisso, 2003).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parenting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Berger and Luckman, 1991) in the context of Israeli TPR cases, meaning how parental behavior and the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are interpreted and narrated in the court decisions.
Background
TPR cases often involve CM (Azar and Benjet, 1994; Azar et al., 1995, 1998; Budd, 2001). While CM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s, studies on TPR have been scant. When conducted, they focused primarily on profiles of foster care children (Noonan and Burke, 2005) and their parents (Meyer et al., 2010; Wattenberg et al., 2001) who were the subject of TPR cases; standards for discussing parental capacity in TPR cases (Azar and Benjet, 1994; Azar et al., 1998; Ben-David, 2013; Benjet and Azar, 2003; Budd, 2001; Budd and Holdsworth, 1996); models for assessing parental capacity (Azar et al., 1998; Benjet and Azar, 2003; Budd et al., 2006; Harnett, 2007); social perceptions embedded in parental incapacity rulings (Ben-David, 2011a; Mass and Nijnatten, 2005);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provided to the courts in TPR cases (Azar et al., 1995, 1998; Benjet and Azar, 2003; Bolton and Lennings, 2010; Budd, 2005; Budd et al., 2006; Melton et al., 1997). None of these studies analyzed the forms of incapable parenting in TPR court cases.
The concept of parental capacity is a central concept and the basis on which decisions in the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are made (Azar et al., 1995, 1998). The literature on forensic assessments (assessments for legal purposes) of parental capacity questions the credibility of parent evaluations due to the methods and practices used by the relevant clinicians (Azar et al., 1998; Budd, 2001, 2005; Budd et al., 2006; Budd and Holdsworth, 1996; Grisso, 2003; Harnett, 2007; Melton et al., 1997). The credibility of such assessments is further weakened by a lack of universal models or standards of minimal parenting competence (e.g. Azar
520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15(4)
et al., 1995, 1998; Ben-David, 2011b; Budd, 2001; Budd and Holdsworth, 1996; Melton et al., 1997). Assessments of parental capacity pose a unique challenge, for they are not based on an exact science but rather on a process that requires the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Azar and Benjet, 1994).
TPR decisions represent a discourse during which judges, mental health experts, and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attempt to determine parental capacity or incapac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used to construct forms of parenting that have social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Throug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rocesses (Berger and Luckman, 1991), professionals interpret parental behavior as capable or incapable. Thes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父母的监护行为是否可以构成犯罪
——基于法院判例中父母监护权终止情形分析
大卫.本.韦德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社会工作学
《社会工作定性研究》(Qualitative Social Work),2016, Vol. 15(4) 518–532
(注:翻译节选自文章第5-10页)
- 研究结果
法律框架中的监护形式
在父母监护权终止(TPR)的案例中,我们得到了亲生父母行使监护权的行为方式可以是消极且有罪的结论。在父母监护权履行不当的整个法律框架下,当事人父母的行为不仅仅被简单定义为不当,同时也被视为有罪。在该案例中,父母被描述为以消极且值得责备的方式明确而绝对地不履行父母义务,而不是由于监护困难或者无法对抗社会环境而不履行父母义务。这份报告确定了四类严重程度不同的不合规范的监护情形:监护能力缺陷,不尽职的监护,危险的监护和有害的监护。以下示例描述了法律中确定的监护情形并讨论其在法律框架中的使用过程。
1、监护能力缺陷。
这个类别涵盖了那些被明确认定为无监护能力的父母,具体表述为父母的监护能力完全丧失或父母的监护能力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监护能力的缺陷往往被认为是忽视孩子需求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父母的监护职能无法得到发挥,孩子的需求才会被严重忽视从而得不到满足。那些用于描述父母功能的语言具有明确的包容性,这导致了结论的单向性,对于提高父母在履行监护职能时的功能性和TPR的必然性是没有帮助的。通常父母的监护障碍归因于父母的病态心理,在具体的案例中法官也认为父亲的监护能力严重受损是因为他不能够把女儿的需求安排在其他需求之前。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情感自我中心主义,被认为是他监护能力缺失的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机械地履责而非情感化地履责削弱了母亲的监护能力。法官认为,社会工作者的证词表明,她作为母亲的履责方式是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为母亲机械地对待她的孩子而没有向他们展示感情。
父母损害行为的概念化意味着存在某种监测父母监护能力执行情况的内在机制,这种在正常的父母监护活动中平稳运行的机制在上述的案例中被严重破坏。父母存在某种障碍意味着父母遭遇到了某种异常状况。在这样的概念中,父母无监护能力被归因于内在的,不可改变的原因,而不是可变的背景原因。因此对于子女需求的漠视归因于无法改变的病态心理,而非社会生态学中所展示的因素,也非父母子女共同生活的过程[1]。在一起严重忽视儿童的案件中,一名法官驳回了将贫困作为可能性解释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忽视对子女最基本的监护职责是非常严重的,即使是最贫穷的家长也完全可以出于意志和奉献精神履行监护职责”。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是父母不愿意充分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贫穷被错误地认为是理解父母行为的一个因素,因为即使是最贫穷的父母也是能够被期望对子女履行义务的。评论没有考虑经济因素对于父母照顾子女的影响,这使得将贫困作为衡量因素的做法值得商榷。
尽管在研究文献中公认大多数可怜的父母都没有虐待他们的孩子[2],但贫穷一直被公认为家庭虐待的主要的危险因素,并与其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例如单亲家庭、父母压力、缺乏社会支持和生活在危险的邻里关系中等[3]。父母现实中的行为与法律要求父母的行为之间的差距使得父母本身更容易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被谴责。
2、不尽职的监护。
这个类别涵盖案例中涉及的未能成功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法官在判例中对此类别进行了这样的陈述:“毫无疑问这位上诉人未能成功地扮演好母亲角色”。 有时失败的监护被描述为缺乏监护能力,并与拥有完整亲子关系的规范的监护形成对比。这种将不充分的监护视为失败并将其归入异常范畴的概念化的理解,表明了存在两种类型的父母,一种是成功遵守了正常父母的行为规则,而另一种则未能遵守。 这也意味着父母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且他们有能力选择更努力地履行监护职责。 再次强调,如前所述,父母被认为是子女权益受损的罪魁祸首,而其他社会生态角色因素则被忽视。
在某些情况下,当父母被给予第二次机会却依旧未能履行好职责,他们的愧疚感会增强:“母亲被给予充分的机会证明她有能力照顾女儿,但她在再次尝试中失败了”; “案件不是关于不给予父母尝试监护未成年人的机会,而是关于给予了机会却依旧未能履行父母职责的情形”。在这些案件中使用的语言与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语言十分相似:诸如“成功”,“失败”,“第二次机会”,“证明自己”等反映矫正的语言。这种语言将父母的能力缺失与社会常态和社会规则规范的偏差等同起来,由此暗示了一个父母行为中的有罪元素。消极的看法掩盖了父母子女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例如,在一个案例中,父亲被描述为未能对他的孩子表现出适当的情绪,而这种失败归因于父亲的情绪自我中心主义:“他无法自己选择孩子的需求,并且无法满足他们基本的情感和发展需求”。在此之前,父亲在法庭上被描述为一个关爱子女的积极的人,“上诉者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对他的孩子没有危险,自己也没有犯罪记录。 专业人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良好的意图,对他的孩子也表现出很多的爱,并且是一个唤起许多人同情的人。 在探访他的孩子时,他们也给了他爱的回馈,同时表达了不能够与父亲待在一起的巨大痛苦。”
尽管对于父亲以及他与孩子的关系的描述是积极的,但法院依然无视父亲对他孩子深厚的爱与情感联系上的失败之间的矛盾。 监护失败的评估产生了父母无能力的结论以及终止父母监护权的结果。将父亲在监护孩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认定为失败,减少了家庭关系本身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它也影响了孩子们对父亲的情感依赖以及增加了他们不得不与父亲分开时的痛苦。“失败”一词具有消极的社会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使用仅针对父母严重不履行自己职责的情形。
3、危险的监护。
危险的监护是指对子女存在风险的监护模式:“专家认为是一种父母子女关系延续过程中产生的危机”; “子女与父亲的接触将会对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在这里,预期风险是孩子的情感发展会受到威胁:“允许孩子留在父母的监护下会危及他的发展和性格成长。父母不能够提供哪怕一点的情感需求,甚至可能损害他(她)的发展”;“父母重新获得子女的监护权可能会危及他的身体健康以及未来的情感发展”。父母的无能通常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伤害:“父母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需求或解决他的痛苦,而如果让父母重新获得子女的监护权,那么子女预计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孩子与他的母亲在一起会对他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事实上,这些声明只是使用了一些戏剧性的、决定性的和过度的语言[4]来对未来可能造成破坏的情形进行预测,并将预期的情况预设为未来必定发生从而生效的现实。决定性的语言表述有助于支持将未成年子女从父母身边剥夺的这种必然性观点。
父母的精神状态或人格缺陷被认为是可能对子女造成危险的父母行为的来源。在一起案件中,法院根据母亲的性格和她与女儿的共生关系,认为这个孩子与母亲生活可能会个性紊乱。法院接受了专家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风险:即这个未成年人不会成功地发展独立的个性并且在发展性格的过程中会出现行为障碍以及与他人难以相处的情形”。在另一起案件中,父母因自己的个性而危及了孩子的教育:“很有可能是因为父母的个性缺陷和身体残疾,父母阻碍了女孩获得适当的教育课程,并伤害了她的安全和最佳利益,虽不是有意的,但还是需要将主因归咎于他们的残疾”。这里的监护危险从全球角度看是由于父母的人格缺陷而危及到了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安全以及最佳利益。
因为所有关于在未来可能伤害儿童的预测都基于潜在的危险的父母行为,所以解释和理解父母行为的方式成为TPR案件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假设是存在一种父母无监护能力或人格缺陷与对孩子潜在的情感造成伤害的直接因果联系。评估父母行为的危险性是基于未来对儿童损害的预测,而这种“未来”的危害是绝对和确定的。当父母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危险”,它产生了一个印象,即迫切需要保护那些被父母威胁到发展的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将孩子与父母分离:“专家预计如果继续维持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则会对孩子造成危险,因此,孩子应该与父母分离并搬到一个收养家庭中”。在这样的案件中,秘密收养被视为确保儿童最佳利益的最佳方式:“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未成年人的正常发展和监护,除非她被一个合适并且愿意给她提供正常生活的的收养家庭收养,她才能完全脱离那个可能伤害她的原生家庭环境”。
4、有害的监护。
这一类别反映了最严重的一类不规范的父母行为。这种情形下父母的行为不再仅仅是可能危害儿童,而是切实地伤害了儿童。针对这一类型的父母行为,法律往往是通过破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来确保孩子的身心安全。在这些案例中,父母的行为被明确界定为伤害孩子的行为:“母亲不仅无视孩子的需求,而且还在伤害这些孩子”。这种伤害通常是孩子心理上的伤害:“与父亲的接触会在情感上和生理上损害孩子”;“父亲与未成年人的关系不利于她,甚至伤害她亦或唤起她对父亲的焦虑与担忧”。在某些案件中,有害的监护被用来描述平衡亲子的利弊关系:“未成年人和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
在这些案例中,父母和孩子之间被视为存在病态的情感关系或者父母的病态人格将导致有害的监护。比方说,父母的角色发生转化并且儿童担当了父母的角色:“当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即女儿满足母亲的需求而不是母亲满足女儿的需求时,母亲和她的女儿的关系是有害的且具有破坏性的”。在另一个案件中,专业评估认为,母亲的情感自我中心主义阻止了她考虑孩子的兴趣:“尽管母亲上诉是为了未成年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她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她向未成年人传达混乱的消息,并且无法意识到她已经造成的伤害[5]”。此时,母亲希望与她的儿子团聚的另一种解释是没有被讨论的,因为她的行为是已经符合了丧失监护能力的评估标准。
鉴于因果解释的确定性,孩子的状态是由父母监护能力的缺失与监护异常引起的,在这样的案件中,结果是确凿的:孩子与父母完全分离。 在最后的案件中,法官的结论是:“母亲不能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hellip;hellip;hellip;她无法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家庭并且善待他”。 在这里父母子女关系的延续被以明确的语言所描述:“如果母亲继续监护孩子,她会对他的发展造成某种严重的情感损害”。 有害的监护情形为永久剥夺父母监护权提供了充分合法的理由。
总而言之,在所有引用的监护类别中,父母的行为与状态都被视为不规范和异常。法院并未使用中性语言来描述父母的功能,也未明确或隐蔽地表述父母伤害儿童或儿童状况来源的行为。即使在具体的案件中他们也没有具体说明父母的性格对孩子造成了伤害,因为这是他们从对父母行为的分类中推断出来的。父母行为归因于内在因素,通常是父母性格缺陷,虽然忽略了背景因素,但依然指出父母是“有罪”,并为父母与孩子的分离设置了场景。因为父母的精神状态或性格缺陷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那么确保孩子的最佳利益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孩子与父母分离。因此,该决定通常不会讨论切断孩子与父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该项研究的几个局限应当被注意。该研究基于法庭判决的内容分析,因此仅限于法院所提供的信息。此外,本文分析的样本代表了在儿童福利人口中心的最具风险性的家庭,因此,概括其他高危人群时应当谨慎适用。该研究没有研究社会背景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在TPR的监护模式下对父母和传统家庭的社会认知。这些领域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便完善TPR模式。
-
贝尔斯基.儿童虐待:一个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J].美国心理学.1980.35(4):320–335. uarr;
-
罗门和西格尔.儿童福利差异性背景下反贫困服务的效果[J].儿童与青年服务评论.2012. 34(9): 1659–1666. uarr;
-
德雷克和琼森.里德.贫穷与儿童虐待.克尔宾和克鲁格曼(编辑)儿童虐待手册.纽约,纽约州:施普林格,第131-148页. uarr;
-
戏剧性的、决定性的和过度的语言,如巨大的危害和不可逆的危害等 uarr;
-
例如,母亲为子女准备了一所房子来居住,但让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无监护权了。 uar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11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